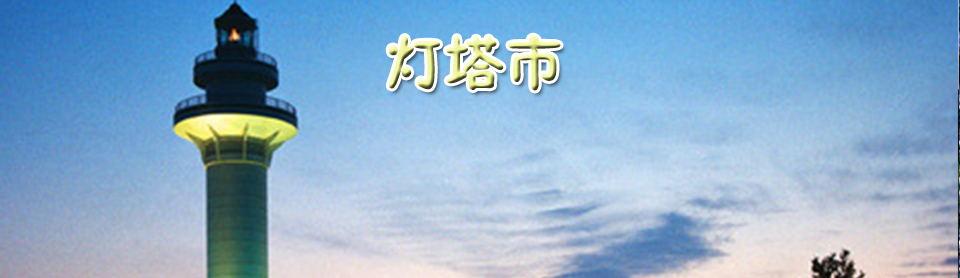灯塔社会的人民会梦到思想警察吗
“您的言论涉嫌对他人人身攻击,请和我们走一趟。”
说起思想警察,从奥威尔的书中走出的词汇似乎总是很容易让人产生奇怪的联想——恐惧、独裁、专制、集权、左翼(越往后的无厘头似乎越能体现一些价值观渗透的影子)——不论如何,思想警察似乎是一个只会出现在需要人为控制思想的地方而产生的令人不快的产物。远到那些反乌托邦游戏、书籍中的报纸审查员与药片,近到一些论调中的“洗脑”甚至是毫无里头的“心灵控制”,不太会有人将思想警察四字与自由民主一类词汇联系到一起,至少,不应当比那些威权专制更加紧密。
是不是总应当有一个社会,按照上述逻辑,它完全看不到思想警察的存在呢?
灯塔国似乎已经成了A国的一个代名词,直接使用可能会产生一定歧义。但我们不妨借用一下这顶帽子,戴到一个我们自行构造的真正所谓灯塔一般的社会之中——真正的是通过某种渠道达成的民主自由灯塔,一个真空中的球形社会。当然,构建这个社会的还是正常的人,我们不能要求他们也是真空中的球形人,不然这个讨论就没有价值了。
这个灯塔社会应当是什么样子的呢?
很显然,它的言论首先当是通畅的,它应为社会的构成提供一个广开讨论的公共空间,一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二来为社会的进步提供思想基础。公共空间应当有其支撑性规则,例如,最基础的,不许骂街,违背者应当受到惩罚。
好吧,针对这样一个基础条例,我们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深入解释?
“不许”这个词大家都理解,“违背者”、“受到惩罚”也都好定义,至于“骂街”,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有人说骂街嘛,就是辱骂,所谓用粗野或带恶意的话谩骂侮辱他人是也。那该如何界定侮辱呢?问候祖宗和生殖行为当然明令禁止,“你今晚必死无疑”的可笑诅咒大概也不被允许(当然,在某些极端思想下这些也是某种自由,但现今我们还是先将其排除在外)。那么,阴阳怪气与冷嘲热讽?大多数人应该是反对的,但是有相当可观的一个少数部分会以“自作多情的解读”为借口不承认阴阳怪气与冷嘲热讽的存在。或者说,他们认同这种行为的存在合理性。
我们继续深入——煽动性、导向性的话语呢?现实中有不少人都否认煽动性话语能够由个体产生,但是鲜有人否认煽动性话语的存在真实性——再不济,诱导式采访、导向性问卷大家总归见到过吧,所谓洗白洗黑,不也是真实存在的吗?语言的力量确能达到改变社会思想导向的作用。我们应该禁止这些话语,当其导向和煽动的事物为针对某个人的辱骂吗?或可以辩解道,我并没有骂他,也并没教唆别人骂他,至于有人骂他,那是他们自身的思想所决定的。加入我们不去禁止这些话语,那很可能引起话题无意义的跑偏与令人作呕的攻击。假如我们明确这些话语不行,如何界定煽动性话语?那样的话,或许整本书也写不下这个话题。
或许有人说,别忘了我们有对话守则啊!我们有议事规则啊!先贤给我们的确留下了宝贵的财富,遗憾的是即便先贤也仅仅规定了不做人身攻击的框架。议事规则中不跑题、不攻击、不超时、不打断更是无细节可考。何谓人身攻击?贴标签扣帽子(你是敌特)算是,攻击固有特征(少条腿还来和我们争,先去拄拐吧)算是,那么“建议你多学习一些逻辑学知识再来同我辩论”算不算是呢?它的确是一个很破坏讨论气氛的话语,而且能够从“质疑攻击对方的学识水平、因学历差异而孤高自傲”来解释,那么我们姑且算它也是。“如果你奉行精神胜利法,那你大可认为你胜利了”算不算是呢?我既可以说是陈述事实,也可以是话中有话,似乎标准就不甚明确了。所谓“法无不可为而为之”,在这样的情况下,显然成文法不能明确的规定出全部应当禁止的内容。何况人的思想是无穷无尽的,今日或许就有更多的骂人方法被发明,我们却无可奈何。
这就陷入了一个法理解决不了抑或无法明确规定的地方。自此我们不出意外是能够想到最具有“灯塔特质”的表决投票类行为来做出判断的。的确,若是大多数人认为这句话是人身攻击,那它似乎不出意外就可以被定义为人身攻击——毕竟语言是用来向人们表达意思的,如果大多数人都没有理解到人身攻击一层的意思,这就是句正常的语言。问题就出现在了这里:第一,冒犯性语句如何界定?每个人自然内心都有一套标尺没错,正如所谓“读空气”是也。但空气不是人人都读得,网络时代更是给读空气凭空增加了一层难度。即便人人都读得,人人内心中对空气的阈值也是不同的。一个人在做类比时说出“xxxxx行为就好像你在学校当着你们班女生的面脱裤子”,那大抵上会被算作冒犯性语句。那么,“xxxxx行为就好像你在学校当着你们班人的面大喊‘我是笨蛋’”,这算不算冒犯性语句呢?可能有些人心中就会打个问号。“xxxxx行为就好像你在学校对着你们班人大喊‘你们是笨蛋’”又算不算冒犯性语句呢?可以看出三例的冒犯性是在逐级递减的,直至有一种状态,或许认为它冒犯与认为它不冒犯的人紧贴于判定标准,使得决定它冒犯与否仅取决于某几个人的想法——就像最后的稻草,他们的意见不论落到哪一边都能产生量变到质变的影响。(我们在这里认为真空中的球形社会是没有“意见领袖”这一情况存在的。考虑到墙倒众人推这一问题,实际会比我们的讨论复杂得多)
然而我们更需要考虑到的是,当决定性意见落到普通人身上,往往这个后果就是不可预测的了。我们赞扬民主,往往不是因为它能带给我们多正确的决定,而是它能带走我们多大的责任,加之屁股决定脑袋,每个人都有双标的可能性。既然我们限定了这不是一个理中客构成的世界,立场、人际关系甚至当日的心情都有可能成为这些决策者的依据。更不巧的是,作为表达的艺术,个人理解的复杂程度是难以想象的,以至于产生如上述的“最后的稻草”时刻的可能性远非如同抛硬币立起来那样微小。有技巧的辩论者可以将对手引入这一尴尬的境地,进而获得自身想要的施加于对手的惩罚。至于没有技巧的——影响他们的只不过不一定是他们的对手而已。在每个人都拥有决策权的语境下,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不喜欢的观点和立场解释成一种攻击嘛。
或许有人会说政治正确、公意暴政也不过是如此,但这是公意暴政所产生的前提——一个合理的、合适的能够产生公意的公共空间。假如连这样一个空间都维系不下来,那么基于其上的任何设计都无从建筑。
可以想象,这时管理话语的责任便落在了每个人的肩上。然而,名为管理话语,欲加之罪便有辞于其中(我想大家也有所了解),加之这一表决之上更不可能叠加任何机构,所谓思想警察,于他们而言倒也不是浪得虚名了。还要不巧的是,这些思想警察既未经过培训,又非专业人士,而只是一个个普通人而已,他们甚至受表决时的保护匿名而不受监督。如此看来,还不如设置一些专业的、经过培训的、公开的、受人监督而不带偏见的裁定者更好。
等等,可那样不就是实实在在的思想警察了吗?
说回来,我们既不能在灯塔社会中设置思想警察,我们也就只能退而求其次的寻找一个“最不坏”的方式,毕竟自我承担自我行为责任是每个健全成年人的义务,因此这种方式更倾向于成为了一个“兜底”方式——被所有人接受的,只能是个“寡而均”的行为。“既要坚决维护少数的发言权,也不能由此因噎废食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一句极其正确的废话,可惜,我们并不能在不专门设置“思想警察”时达到这个境界。若是想要一个有着正常秩序的公共空间,言论与思想的管理者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它有一定的功能在于判定不可表述的思想和话语,但更多的作用在于判定什么思想和话语能够被表述而不应遭到质疑和惩罚。然而,这种存在势必侵害了全体其他人民的潜在利益(利用表决驱赶异己的利益、说出不合时宜的话语而可能的不被惩罚的利益),因而不太可能民主的存在下来。一个能够存续的社会不能没有思想管理,法律条文又不容许管理思想,那大家就都要成为管理者——既然大家都是思想警察,那就没有人是思想警察咯!
理性和感性是一个十分人为的界定方式。我们既不能从中划定一个明确的界限,更不能通过明白准确的文字陈述出他们的性质。更令人沮丧的是,理性和感性不一定是对立的,一个人可以感性的理性,也可以理性的感性,甚至将二者糅合在一起,能够达到初期的表达效果,引人垂涎。这其实是本文所要表达的一个观点,即我们除非让受过良好教育而又受到合理监督的少数人来裁定一句话是否属于理性讨论的一部分,通过其他任何方式裁定的所谓“人身攻击”、“歧视”等都是具有着莫大的不确定性与歧义的,都是会严重的影响思想市场的内容与活力的。然而,这种“监察者”若是要做到对权力的不滥用,怕不是也要是真空中的球形人才行。因此,既然无法实践一个完全无害的言论引导策略,我们就不应当视思想警察这一现象为如临大敌之兆。不如,我们使用自己的思想从单纯的利弊权衡角度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允许一个或几个受到监督(可以考虑十分严酷的监督,然而又要赋予其足够的自由裁量权)的思想警察的存在对思想市场的影响更大,还是采取民主裁定抑或不受监督的“全民皆兵”政策对思想市场的影响更大?这个影响应当算上人身伤害,应当算上寒蝉效应,甚至应当算上你在晚餐时间想和自己亲人发表一个观点,然后一想,还是算了。
灯塔社会的人民大概不会意识到自己梦到了思想警察,不过,他们梦到的每个人都是思想警察。
*封面图来自网络
编者突然想起她来。绘:虽华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转载请注明:http://www.dengtazx.com/dtsxw/6776.html